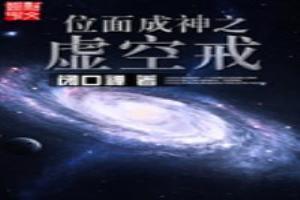放棄白月光後:發現夫君黑化了第一百九十章 勝券在握
再則說了,不就寫詩諷刺了幾句,又不是什麼大事。
人家相府都能忍,怎麼到他這就忍不了了?
李太傅倒是沒忍,不也沒壓的住馮閣老?
想起馮閣老那罵人時候的樣子,連父就是一陣陣的頭疼。
連母還想說什麼,卻被安紅韶拉了一下,「沒想到,父親也聽說了惠安縣主的事。」
隨即回頭,將自己整理的冊子交給了連父,昨個她讓冬青砸銀子,自是知道,這一本冊子從從前的三文錢,已經長到了八文錢。
也估略算出了,這一日能賣出多少去。
大概是庶出的原由,看見一個東西安紅韶總是不由自主的想想,得需要多少銀錢。
所以,這賬本安紅韶是算出來了。
鬧成這樣,說書的先生怕也會說起這事,粗略估計,能聽過這些的,得有近八萬人。
等著科考結束,在從京城傳到外頭,不可計量。
連父翻看著安紅韶擬出的賬本,微微皺眉,「你的意思是?」
安紅韶重重點頭,確實如此,科考的事是馮閣老主理,可是,科考之外的東西呢?
這兩本冊子傳的這麼遠廣,亦那個什麼寶釧為例,已經有人開始想法子投機取巧了,若是不整治,人人都來效仿,那才是國之危矣。
本來,結果已經擺在這了,這是歸連父管的,完全可以下尚書令,可偏偏,李太傅上書,卻被馮閣老駁斥,既在朝堂上討論了,連父還是該同聖上稟報。
這事,是連父分內的事。
「今個惠安縣主派人過來了,想來相府對此事,也頗有微詞。」安紅韶一頓接著才又說到,「二舅父那邊恰在戶部辦差,不知道父親覺得,是否需要問問,這賺的這些銀錢,該是多少地界才能稅收上來?」
安紅韶說是詢問,卻是直接將路指明了。
連父這個人辦事謹慎,為了避免他有後顧之憂,安紅韶直接點他去相府探口風,如果明日一早,大家都能參一本,勝算更大。
二來,連父怕旁人說他公私不分,那就將事情說的越大越好。
大家都該規規矩矩的辦事,不能說因為你胡亂的寫一些個下三濫的書,這就賺銀錢了,銀子賺的這麼輕易,以後誰讀書是為了考功名,都寫這種東西就算了。
如此一說,那什麼寶釧的書是源頭,而這個嘲笑安紅韶的詩句,就成了跟風。
文人,你可以批判你所以看的不公的東西,可是你不能信口雌黃的胡言亂語。
若是朝堂風氣變了,那就是禮部尚書的失職,真若縱容下去,他這個禮部尚書也不用做了。
「朝堂的事,我自有安排。」連父說完,當著安紅韶的面,將那冊子合上,而後叫了席杉過來,連夜查書局,看看這上頭的寫的是否準確。
交代完席杉,連父又讓人叫了連如信過來。
無論是相府還是太傅府,連父肯定要親自去的,所以家裡的事,得趕緊得安排了。
只是沒想到,連如信過來了不說,周氏也跟著了,這也就罷了,周氏還讓乳娘帶著連婧函過來。
連父在看見來了這麼些人的時候,好不容易緩和下來的臉,隨即沉了下來。
可是孫女跟前,總不好說什麼,待大房這邊見了禮,周氏才笑著說到,「婧函這孩子一直念叨,好些日子沒有瞧見祖父了,沒想到這么小的孩子,還懂得想人了。」
連父扯了扯嘴角,總不好嚴肅的嚇到孩子,伸手招呼婧函坐過來,「是嗎,想祖父了?」
將婧函往自己腿上一放,卻沒再逗她,而是看向連如信,「你今個連夜寫出一篇,恩師賦來,一定要寫的情深,寫的感人。」
尊師重道,才是大家要學的。
而不是,只想著天上掉餡餅。
說完之後,「我今個估摸得回來晚了,你再給我擬兩篇摺子,一篇駁斥近來之事,一篇直接參馮閣老。」
這詩鬧得沸沸揚揚的,連如信怎麼可能不知道。
第一百九十章 勝券在握
html|sitemap|shenma-sitemap|shenma-sitemap-new|sitemap50000|map|map50000
我的書架 電腦版 手機版:https://twm.21zw.net/0.017s 3.7871MB